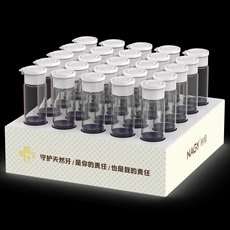毛泽东,一个坚守者的孤独

毛泽东的晚年是孤独的。这似乎是一个无疑问的事实。
1974年五月,作为一名学养深厚的诗人,毛泽东专门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了大字本的庾信《枯树赋》、谢庄《月赋》、谢慧莲《雪赋》以及江淹的《别赋》、《恨赋》。(见《毛泽东年谱》下第六卷,第5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1版)。有人认为,毛泽东此时选阅的这几篇古韵文,情感悲凉沉郁,恰恰体现了毛泽东晚年孤寂、伤感的心态。“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树赋》中的这些名句,据说就曾让这位共和国的领袖无比伤感,甚至在读后几度哽咽。
于是,有人突发奇想,用毛泽东孤寂的晚年生活和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幸福的、充满亲情的晚年生活进行了一番对比,并在对比之余大发感概:“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政治的追求当然是难以放弃、不能割舍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政治家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梦想。但亲情呢?家庭呢?或许还应该有这些政治家的爱情。失去这些,或者所有这些又极其不完整呢?这对政治家的命运又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2014年8月27日《人民日报》文章)
这是一个看似很有道理,实则极端荒谬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他的一生已经完全奉献给了他所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在他的晚年,毛泽东怀着将自己彻底粉碎之决心,以一己之力,同人类世界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绝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私有观念作战。他既是一个孤独的战士,更是一个为实现“世界大同”理想而不屈奋斗的坚守者。
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晚年,以他的智慧与威望,完全可以选择一种和邓小平一样,甚至比邓小平的晚年生活还要滋润的“融融泄泄”的幸福人生。君不见,毛泽东虽然在革命的一生中失去了很多亲人,但是在他的晚年,他的膝下尚有一子二女一孙,亲近的子侄之辈更是以十数计,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尽情地享受“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在党内,毛泽东威望如日中天,只要他愿意,和党内任何一个派别、任何一个人结下超越一般同志关系的友谊都是易如反掌的小事;同时,按照毛泽东身边人的回忆,在生活中,毛泽东同样是一个“富有情趣的人”,“他谈吐幽默,跟身边的人非常随和,喜欢游泳、爬山,平时爱和身边的人逗逗趣,大家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见《张耀祠回忆录》第18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6月1版),只要他愿意,凭他的智慧,成为诸如桥牌之类游戏的高手亦绝非难事。
然而,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为了避免自己的子女后辈成为拥有特权的特殊阶层,他要求他们在生活上要简朴,在组建家庭时要尽量选择普通的工农兵家庭,为了防止他们产生特权意识,他甚至有意地将他们同自己的生活隔绝开来;为了避免党内出现以私利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毛泽东一生坚决反对拉帮结派。对于党内拉帮结派者,他曾尖锐地讽刺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正如他的警卫战士回忆的那样,毛泽东一生中和很多党外人士(如章士钊、黄炎培)都有过私交,日常生活中亦多有书信往来,但在党内,毛泽东却从不串门,从不发展超越一般同志关系的所谓“友情”。就这样,为了确保自己作为执政者的公正,为了防止特权阶层的形成,为了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毛泽东作为一名彻底的革命者,在自己的晚年坚守着孤独与寂寞。
但是,同样是这个毛泽东,却在自己孤寂的晚年,时时刻刻心系着自己的人民,渴望置身于人民群众的海洋之中。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在农村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与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生活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见《毛泽东传》第六卷第26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往事越过四十年,在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如果还有一个普通百姓,想要和共和国的领袖直接通信并得到回复,其难度相信不用笔者说明,各位读者也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作为老人,毛泽东从不否认自己在晚年也有脆弱的一面。但是这种脆弱却始终是和人民群众的安危联系在一起的。1975年夏天,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中几十名群众遇难的内部报道时,毛泽东情不自禁,不顾自己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眼含热泪,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见《毛泽东传》第六卷第27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
据曾为毛泽东做过眼科手术的唐由之医生的回忆,他曾亲历过毛泽东晚年读诗哽咽的场面。1975年7月,唐由之陪护在毛泽东身边,突然,他被一阵呜咽声吓住了。等他抬头一看,只见毛泽东手捧书籍,老泪纵横,已是泣不成声。在唐由之的劝解下,过了许久,毛泽东的情绪才稍许平静。唐由之近前发现,引起毛泽东情感变化的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这是一首感叹山河破碎,祖国不能统一的诗作(见顾保孜《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6月1版)。作为一名早已看淡生死的革命者,一名情感丰富的诗人,毛泽东在自己的晚年读诗哽咽,难道仅仅就是由于他孤寂的晚年生活造成的吗?难道不是他对自己作为常人,必须遵从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不能完全实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理想与抱负,而发出的一种类似“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浩叹吗?
由此,笔者不禁想起前苏联官员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一段记叙。他说:“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就是这样彼此合作的。勃列日涅夫对他们可谓言听计从,因为给他出主意的是他的三个可靠的朋友——尤拉、季乌和安德留沙(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的昵称)。
哪些人是勃列日涅夫家宴的常客呢?勃列日涅夫的儿媳想都不想便回答道:常到家里来吃饭的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我从未见拉西多夫和库纳耶夫来过。见过晓洛克夫一次......”
有时这位儿媳也会告诉自己的公公(勃列日涅夫)‘安德留沙.葛罗米柯叫我们去吃饭。’勃列日涅夫马上就会做出反应‘好啊!可为什么要去他那儿?就让他到我们这儿来吃饭吧。’,多么闲适的生活啊!”(见《苏联外交秘闻》第277页,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相比毛泽东孤寂的晚年,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勃列日涅夫的晚年生活真可谓“其乐融融”了。然而就是在这段“其乐融融”的日子里,整个苏联社会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特权阶层横行霸道,人民群众理想破灭,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滑,直至沦丧。勃列日涅夫死后不到十年,苏联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大厦便轰然倒塌,消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这是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同志的晚年是孤独的,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现实。但是透过毛泽东远去的孤独的背影,我仿佛听见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在说:“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毛泽东:一个理想坚守者的孤独!
来源于红歌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