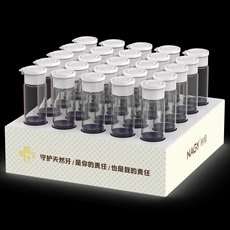口腔微生物与肠道微生物的关系 科贸嘉友官网收录
[摘要] 口腔和肠道是人体消化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腔微生物和肠道微生物的相互关系和致病共性已成为近年来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近期研究进展,对口腔微生物和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相互定植和致病作用,以及两者与系统性疾病的相关性进行综述。
人类自身的数十万亿细胞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构成了人类的“第一基因组”,而每个个体携带的超过10 000种、总量数十亿的微生物遗传信息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第二基因组”,即人体微生物组[1]。人类第一基因组和第二基因组共同决定了人体疾病与健康状态。200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启动“人类微生物组计划”(Human Microbiome Project,HMP),旨在通过绘制人体五大部位(口腔、鼻腔、阴道、肠道、皮肤)微生物基因组结构,解析微生物菌群结构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2]。人类微生物组计划不仅建立了权威的样本采集方法和纳入排除标准,规范了高通量测序流程,更获得了丰富的人类微生物组资源,可为后续的科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3-6]。2015年8月美国又启动“全民个体微生物组检测项目”,开展大规模人群微生物群落信息研究,旨在以口腔、皮肤及肠道微生物群落为主要研究靶点,将HMP研究结果进行临床转化,从“第二基因组”中寻找更加精准的疾病预警分子标记。
自Marshall和Krajden分别相继从胃和口腔中培养分离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 pylori)[7-8]后,大量研究发现牙周组织中幽门螺杆菌的定植是牙周炎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9-13],口腔定植的幽门螺杆菌与胃食管感染密不可分[14-15]。尽管目前对口腔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但上述研究结果提示人体口腔、鼻腔、阴道、肠道、皮肤等五大部位的微生物可能在结构和功能上存在一定重叠,口腔微生物和胃肠道微生物可以交互影响,在疾病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口腔和肠道是人体消化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体最主要的两大微生物生态位点,两者定植微生物群落间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近年来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热点。
1 口腔微生物和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
1.1 口腔微生物群落
作为人体微生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腔微生物群落因取材方便、与口腔及全身健康关系密切,成为HMP及“全民个体微生物组检测项目”的重点关注对象。口腔微生物多以生物膜形式组成复杂群落,行使微生物生理学功能。当与宿主处于平衡状态时,口腔微生物群落可阻止外源性致病菌的入侵,发挥生理性屏障作用;当微生物群落与宿主间生态关系失衡时,可诱发多种口腔慢性感染性疾病,包括龋病、牙周病、牙髓根尖周病、智齿冠周炎、颌骨骨髓炎等,严重危害口腔健康。更为重要的是,口腔微生物可作病灶,与全身系统性疾病关系密切。近期研究发现,口腔微生物与口腔癌[16]、糖尿病[17]、类风湿性关节炎[18]等疾病有着密切联系,可作为上述疾病的潜在生物学标记。
口腔微生态系作为仅次于肠道微生态系的复杂系统,其不同生态位点内微生物群落物种组成及基因种类均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与宿主的健康及疾病状态相关,同时受到宿主年龄、性别、牙列状态、民族、居住区域等遗传及环境因素的影响。课题组通过各种高通量分析技术(454焦磷酸测序,illumina测序以及GeoChip微生物功能基因组芯片),在宏基因组学层面对口腔微生物群落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发现,口腔典型微生态境内细菌的分布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厚壁菌为唾液及颊黏膜的优势细菌门,而变形菌、厚壁菌、拟杆菌及梭杆菌为龈上菌斑优势菌门;口腔细菌组成随着人的年龄及牙列状态改变呈现波动状态,颊黏膜菌群中螺旋体的丰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递增趋势[19]。目前拥有人类口腔细菌16S rRNA和基因组资源最全的数据库是由美国Forsyth研究所和英国国王学院联合在NIH牙颅颌面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ental and Craniofacial Research,NIDCR)建立的人类口腔微生物组数据库(Human Oral Microbiome Database,HOMD;www.HOMD. org)[20]。该数据库共有13门691种口腔细菌,其中344种已命名,112种可培养未命名,232种不可培养。
1.2 肠道微生物群落
从胃幽门至肛门的肠道是人体消化道最长、功能最重要的一段。肠道微生物组成人体最大的微生态系统,定植细菌超过35 000种[21]。肠道细菌主要由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组成,其次是放线菌门和疣微菌门。生理状态下,肠道共生菌参与食物消化和药物代谢,调控宿主免疫,阻止病原体侵入组织和器官。该生态平衡一旦被打破,致病菌将占据主导地位,细菌毒素和代谢物质等有害因素侵袭肠上皮细胞,可引起炎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应激性结肠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结肠癌及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22]。
肠道微生物群落物种组成及基因种类存在时空差异。小肠、大肠和直肠作为肠道的三部分,其微生物丛组成和结构具有较大差异,与每部分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23]。不同个体中肠道微生物组成差异较大,而单一个体相对稳定[24]。饮食、抗生素使用或宿主生理状态均可能导致肠道微生物的一过性变化。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建立与唾液微生物群落类似,成人平均每天产生>1 000 mL唾液,几乎全部进入胃肠道,因此唾液细菌有很大机会进入并定植于肠道,提示唾液微生物群落可在一定程度影响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发展[25]。
随着美国HMP计划和欧洲人体肠道宏基因组计划(Metagenomics of the Human Intestinal Tract,MetaHIT)的开展,人类对肠道微生物的理解更加深入。两项大规模人群计划从基因的水平系统探索了肠道微生物的结构和功能。发现肠道微生物群落组成具有很大个体差异,双生子肠道中相同的细菌种类少于50%,相同的病毒序列则更少。遗传因素在肠道菌群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宿主染色体上某些特殊位点可影响微生物群落的组成[26]。在微生物群落功能层面,学者们对肠道微生物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对疾病的防治有了新的手段,近期研究[27]发现,可以通过益生菌、某些抗糖尿病药和粪菌移植等手段,改变肠道代谢状况,从而干预代谢紊乱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
2 口腔微生物与肠道微生物相互定植及致病作用
口腔细菌是否可通过进食和唾液吞咽进入胃肠道定植,肠道细菌是否通过粪-口途径或者胃镜检查定植于口腔?口腔和肠道微生物相互定植后是否影响原来的生态平衡而引起相应疾病?尽管针对上述科学问题尚无明确的结论,但近期大量研究结果对深入了解口腔与肠道微生物的交互作用提供重要线索。
2.1 口腔微生物在肠道中定植
牙周病被公认为是许多系统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其主要致病菌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在口腔中的定植可导致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紊乱,杆菌门数量增加,厚壁菌门数量减少,血清内毒素水平增加,导致肠道炎症发生[28]。牙龈卟啉单胞菌还可入侵肝脏,引起相关疾病[28]。有学者[29]发现肝硬化患者肠道微生物组结构改变主要归因于大量口腔细菌入侵肠道。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是牙周病的另一个重要相关菌。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在肠道中检测出,但该细菌可定植于肠道,在结直肠肿瘤和炎性肠病中发挥重要作用[30]。近期研究[31]证实,具核梭杆菌可抑制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促进结直肠癌的发生,并与结肠癌的预后密切相关。
阑尾是人体微生物的储备库,定植于阑尾的微生物在特定情况下可重新定植于胃肠道。学者[32]研究了急性阑尾炎患者阑尾的微生物组成,发现厚壁菌门是主要定植菌,其次是大量变形菌门、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等肠道菌群。同时检出了许多口腔常驻细菌,如双球菌属、微单胞菌属和梭杆菌属等,且梭杆菌属与阑尾炎严重程度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33]发现,阑尾炎患者阑尾切除样本中梭杆菌属数量较健康人群显著增加,拟杆菌属数量显著减少,并检出卟啉单胞菌属定植。
唾液链球菌(Streptococcus salivarius)是口腔早期定植菌,可定植于肠道中,下调小肠上皮细胞的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在肠道炎症反应和内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34]。Zhang等[35]通过对肝硬化患者以及肝硬化并发肝性脑病患者粪便微生物群落16S rRNA序列分析,发现唾液链球菌可移位到肝硬化患者肠道并过度增殖,是肝硬化以及肝硬化并发肝性脑病的重要诱因。白色假丝酵母菌在义齿性口炎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Sugita等[36]将其接种到无菌鼠口腔中,在小鼠粪便中检测到该菌,发现它在肠道中的定植与易感人群的食物过敏密切相关。有学者[37]通过人群问卷调查发现,不良口腔卫生保健行为可改变口腔菌丛,引起肠道微生物失衡,导致IBD的发生。
2.2 肠道微生物在口腔中定植
肠道微生物几乎不能在口腔定植。He等[38]在小鼠口内成功建立了一个包含10种以上细菌的稳定微生物群落,该群落可识别大肠埃希菌表面脂多糖,产生H2O2抵御小鼠肠道来源大肠埃希菌或外源接种的大肠埃希菌标准株在口腔的定植。尽管如此,肠道微生物可间接影响口腔微生物群落结构。IBD被公认为是肠道菌群紊乱引起宿主免疫反应改变,进而引起的炎症反应。IBD患者常伴有唾液微生物组成变化和相应的口腔症状,提示病理状态下肠道微生物可能通过影响宿主免疫,直接或间接影响口腔微生物群落组成[25]。
3 口腔微生物和肠道微生物与系统性疾病的相关性
随着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微生物在系统性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口腔微生物和肠道微生物可单独引起一系列系统性疾病,但两者是否同时参与系统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并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亟待深入系统的研究。
3.1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又称循环系统疾病,指发生在人体运送血液的器官和组织,包括心脏、血管(动脉、静脉、微血管)等疾病的总称。牙周致病菌(尤其是牙周“红色复合体”)、牙菌斑微生物所导致的炎症反应、免疫反应、生态失衡和胆固醇水平变化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肠道微生物可通过调控肥胖、胰岛素抗性、血脂浓度等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参与该类疾病的发生发展[39]。Armingohar等[40]发现伴有牙周炎的血管疾病患者中细菌数量和多样性比不伴有牙周炎的血管疾病患者多,样本中不仅存在大量口腔共生菌,还频繁检测出肠杆菌,提示肠道微生物和口腔微生物均可能参与到血管疾病的发生。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的一类常见心血管疾病,发病机制上属于代谢和炎性疾病,患者血浆胆固醇水平升高,动脉壁巨噬细胞富集[41]。目前已有大量研究[42]证实牙周微生物与该病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近期有学者发现肠道微生物也参与其中。Koren等[43]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动脉硬化斑块中存在细菌,细菌DNA的量与斑块中白细胞的量相关。运用细菌16S rRNA测序深入分析斑块中细菌的组成,发现所有斑块中均存在金色单胞菌属(Chryseomonas),大部分斑块中存在韦荣球菌属(Veillonella)和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两者的丰度与其在口腔中的丰度密切相关。动脉粥样斑块中另外几种常见细菌种型也在同一个体口腔或肠道样本中检出,说明斑块中细菌来源除口腔外,还有肠道。口腔和肠道中某些细菌门类与患者血浆胆固醇水平相关,提示口腔和肠道微生物群落与动脉粥样硬化的生物标志物具有一定关联。
3.2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
RA是一类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数千万人,并由于心脑血管等全身性并发症导致大量患者死亡。微生物因素作为该疾病的激发因子之一,在疾病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近期一项研究利用宏基因组鸟枪法测序(metagenomic shotgun sequencing)和元基因组关联分析(meta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MGWAS)检测RA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粪便、牙齿、唾液样本中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功能。研究[18]发现口腔微生物组和肠道微生物组在丰度和功能上存在重叠。两者的改变可将RA患者区分于健康人群。这些微生物特异性改变包括患者口腔和肠道中嗜血菌属(Haemophilus)减少,唾液乳杆菌(Lactobacillus salivarius)数量增加,两个位点微生物群落中铁、硫、锌等离子和精氨酸转运/代谢发生改变。RA经过治疗后,微生物组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提示口腔和肠道微生物群落的特异性改变可以作为预测和诊断RA的潜在手段[18]。
口腔微生物中牙龈卟啉单胞菌与RA的发生密切相关。牙龈卟啉单胞菌可以产生肽精氨酸脱亚胺酶(peptidylarginine deiminase),使精氨酸转化为瓜氨酸,许多黏膜蛋白被瓜氨酸化后可使体内产生抗瓜氨酸化蛋白抗体(anti-citriullinated protein antibodies,ACPA),后者是RA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44]。肠道微生物主要通过大量革兰阴性菌的代谢毒物进入血液循环,进而影响RA的发生、发展[45]。目前尚不能断定肠道菌群生态紊乱是RA的直接致病因素,还是其通过导致局部或全身炎症而间接诱发RA。此外,RA患者肠道菌群改变所导致的酶效应和代谢改变仍待深入研究。
3.3 肝硬化
肝硬化(hepatic sclerosis)是临床常见的慢性进行性肝病,由一种或多种病因长期或反复作用形成的弥漫性肝损害,肝性脑病是肝硬化的常见并发症,是肝硬化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变化可作为肝硬化发病标志。李兰娟院士课题组比较了肝硬化患者和健康人群粪便微生物组成,发现肝硬化患者拟杆菌门丰度显著下降,变形菌门和梭杆菌门显著上升。在细菌科水平,肝硬化患者肠杆菌科、韦荣球菌科及链球菌科检出率显著增高,毛螺旋菌科丰度下降,这4个细菌科水平的变化与肝硬化诊断及预后密切相关[46]。有学者[29]发现肝硬化患者丰度较高的肠道微生物中有54%来源于口腔,其中优势菌主要是口腔唾液链球菌和韦荣菌属,提示口腔细菌移殖到肠道在肝硬化发病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唾液链球菌和韦荣菌属可作为诊断肝硬化的微生物标记。Patel等[47]也发现口腔唾液链球菌是肝硬化及并发肝性脑病患者早期监测和后期疗效评估的重要微生物标记。此外,有学者[48]发现肝硬化患者唾液和粪便中土著菌丰度降低,肠杆菌和肠球菌数量增加,提示肝硬化发生、发展与口腔和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3.4 其他
唾液乳杆菌Ren(Lactobacillus salivarius Ren)是分离于我国巴马少数民族的一株益生菌,它是口腔和肠道的土著菌[49]。研究发现该菌不仅可有效预防口腔癌发生[50],还可逆转1,2-二甲基肼(1,2-dimethyl hydrazine)诱导的结肠癌模型中小鼠肠道菌丛的变化,促进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恢复到正常水平[51]。口腔微生物黄褐二氧化碳嗜纤维菌(Capnocytophaga ochracea)和肠道大肠埃希菌可以表达特异性肽激活T细胞反应,诱发舍格伦综合征(Sj?gren’s syndrome)[52]。此外,Saxena等[53]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患者口腔和肠道微生物发生改变,细菌和病毒之间的串话可望为HIV感染提供新的诊断和治疗手段。
4 小结
随着高通量组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HMP和MetaHIT等项目的推动,人类对口腔和肠道微生物群落的认识不断深入,获得了海量大数据信息。通过整合和挖掘这些生物学大数据资源,发现口腔微生物和肠道微生物具有各自相对稳定的群落结构和组成,并发挥相应的功能。口腔微生物可定植于肠道成为其微生物群落中的一员,影响疾病的发生;两者受某些系统性疾病的影响,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口腔微生物和肠道微生物的交互作用,以及两者所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的代谢通路、致病机制亟待深入研究。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世纪80年代末率先在国内开展口腔微生物生理定植与致病机制的系统研究,目前已初步建立了中国人口腔微生物资源数据库(http://www.computationalbioenergy.org./jinggctest/index.php),并正着手建立中国人唾液样本库,基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与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开展唾液临床诊疗新技术,开展口腔微生物与肠道微生物定植与交互作用、肠道微生物与口腔疾病易感性等热点问题的前瞻性探索,旨在解析疾病发生共性病理新机制,开发口腔甚至全身疾病防治临床新技术,实现对口腔疾病、肠道疾病以及相关全身疾病的风险评估、早期诊断和预后预测,切实推动疾病的个体化精准医疗。
[参考文献](略)
作者:程兴群 徐欣 周学东
作者单位: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口腔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成都 610041
详见《华西口腔医学杂志》2017年6月第35卷第3期